《被移植的树 李浩》阅读答案
李浩
我要说的并不是树。至少不单单是树,我要说的是另外的人和事。
有时,在春天或者秋天的公路上,我会遇到装载大树的卡车。那些树已经足够高大,甚至都小有沧桑,硕大的树根和根部的泥土被粗草绳仔细地包裹起来,伤掉的细根似可忽略不计。它们将会被移植到城市,路边或者公园,携带着这一小点儿的
“
故土
”
,然后开始新的生长。它们会长得更高大些,部分的根须会获得延展,把原属于异乡的土也一并紧紧抓牢。
我要说的并不是树。我要说的,是贵州,安顺,一个叫屯堡的地方,和那里生活的
“
少数民族
”
。说他们是
“
少数民族
”
并不是我个人的发现,在贵州的朋友特别向我指认,然后告诉我,屯堡居住的
“
少数民族
”
其实是更严格意义上的汉人,他们的祖上来自明朝时的中原,是征战和屯兵的结果。
有战,有和,还得有驻守。于是,这些来自中原的将士被安插在屯堡,之后他们的家人,妻儿,或者在中原被招募、被迁徙的男男女女也跟着来到了这里,就像
……
就像树的移植,是的,就像是树的移植,他们在这个完全异乡的地方扎下了根,在这块异乡,他们部分的根须获得了伸展,被和那小部分的故土一起紧紧抓牢。
那一小点儿的故土:这些迁徙者和他们的子孙,曾经固执地将它固执地守住,让它尽可能地不融化,不变异
——
这是他们从中原所带过来的,我们可以从这份固执中看到迁徙者们的
“
念念不忘
”
。那一小点儿的故土是:语言,服装和发式,被称为
“
地戏
”
的传统戏剧,生活习惯,也许还包括家族观念,邻里关系
……
进屯堡的路上,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在那里,我见到了屯堡人的传统服饰,见到了地戏表演用的面具。据说,地戏表演内容以
“
杨家将
”
、
“
薛家将
”
等居多,很中原化,或者说很
“
凤阳化
”——
在我的观看中,我承认,这一切,对我这个汉人来说几乎是全然陌生的,惊异的,我用出的目光是那种
……
就如同对苗、藏、日耳曼民族的观看与探寻,我努力在其中寻找着不同,加入着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是的,这一小点儿的故土在一个中原的汉人那里也变得古老而新鲜了,变得异质了,他们固执的坚守竟使得自己完全地区别于
“
中原
”
。
这种坚守:使他们这些人成为恒久的
“
少数民族
”
,成为恒久的异乡人,即使在他们生长的这片土地上,我想他们的归属和认同也不会强烈,他们大约有一种永恒性的局外感,这几乎是一块
“
飞地
”
,它陷入于其他民族的周围,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警惕甚至敌意。在云山屯(屯堡中的一个更小的地方,大约属于它的八分之一),安顺的朋友向我介绍,在某个历史时期,屯堡曾先后被当地的另外的土著攻破,最后所有活着的屯堡人都集中到了易守难攻的云山屯,做着顽强的、攸关生死的抵抗
……
朋友们说得轻描淡写,但在我听来,却足够动魄。我回头看那些古老安静的房子,想象自己是一个青的屯堡人在寨门上警戒,绷紧神经,日日夜夜
……
毕竟,他们是被安插到这里来的,移植到这里来的,虽然那是他们祖辈的事了,虽然,他们的祖辈肩负着使命和荣耀。在不被融合、融化的固执里,除了怀乡这种病症,我想大约还有着某种精神上的高傲。这点,毋庸讳言。
我继续说树的移植,说屯堡。说树的枝叶下那一小片的故土。在我来到屯堡的时候遭遇的是一场大雾,我们在雾中上山,这几乎要打断我们的行程,好在,它缓缓地散着。有雾掩映的屯堡其实更有独特的美,有它自己的时间史,有它高中.初中阅读答案自己的时间长度和额外宽度,有单独属于它的时间黏稠
——
这点,在云山屯更为明显,更为强烈。走在古老的石阶上,走在石质的、木质的古老房子之间,那种时间的黏稠感是显见的,它甚至有了弯曲,起伏,让人仿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中,仿若,进入到了历史。何况那雾。遮住了向更远处望见的雾。在
“
我们的
”
时间之外,这是屯堡给我的强烈感觉。当战事平息,那些背井离乡的人在这片陌生、偏僻的地方得到安顿,修养,生息,刻意而固执地保持着祖辈的文化和习惯,慢慢,它和
“
我们的
”
时间脱开了,它有了自己的坚固。在云山屯,或者我所走过的其他几个屯堡,它们保留的是明时的建筑,至少是明时的风格,它们也成为树的根部的小片故土,慰藉着一代一代的怀乡病。六百,在屯堡之外已几度风雨变幻,云卷云舒,当他们把和
“
外界
”
的路一一打开,突然发现,那个臆想的、被记忆的
“
故土
”
早已没有了当初的模样。
他们打量我这个来自北方的汉人,也许就像打量一个
“
外族人
”
,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着特别的、大致相同的血缘。那些生活在贵州、安顺的另外汉人也大抵如此。
云山屯,它的静寂让我意外。那种静寂应当只有梦里才有,它多少已不属于凡尘,尤其对我这样当下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它的静寂更凸显了它的质感和美,我想是这样的,石寨在别处也有所见,但像如此安静的,似乎只有此处。它几乎是空的,旷的,单独属于我们这少数几位来访者的,它允许你向任何一处探幽。
远处有些许的鸡鸣,引得近处石房角落里的鸡也跟着叫起来,那一刻,我都想停下来,止住呼吸
——
在云山屯,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任何一个人都是外在于这个时间这片土地的,在进入到它们的地域里,我们必须保证对
“
主人
”
的敬重使它们免被打扰。我们走远些的时候,回头,有几只鸡缓缓走上了石阶,走在我们刚走过的路上,它们安然的样子让人感动。
朋友们说,这座屯堡除了少数的老人外,其他的人多数已经下山,他们接受与
“
我们
”
同样的教育,穿同样的服装,喝啤酒,泡吧,上网,经商或外出打工
……
屯堡的
“
少数民族
”
正在普遍地汉化,重新成为汉人。屯堡,用不了几,就会变成一个完全的象征,一种旅游资源,一种可在
“
外人
”
面前展示的、不具根脉感的文化。
在屯堡博物馆里,负责讲解的屯堡小姑娘给我们叙述的只有博物馆墙壁文字上提供的那些,她远不如一个
“
外人
”
,博学的杜应国先生对屯堡知道得更多,包括她服饰中的文化内含
——
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指责,甚至有小小的欣慰。当然,我对这份欣慰也有些忐忑和质疑。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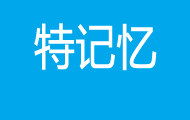 学习方法网
学习方法网